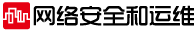面對數字經濟時代全球價值鏈的全新特征與新風險以及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我國產業與微觀企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需要在生產要素層面進一步強化數字要素的第四類生產要素在數字創新驅動發展要素中的核心地位,在產業層面,強化數字經濟對產業的賦能效應,即產業數字化與數字化產業雙輪驅動打造面向國內大循環的產業鏈與創新鏈共促機制;在微觀企業層面,強化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建設驅動創新引領,破解關鍵核心技術的“卡脖子”問題。
一、數字經濟發展以及對全球價值鏈的影響趨勢
數字經濟對全球價值鏈的影響過程與影響機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數字經濟對全球價值鏈的成本節約機制。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技術能夠影響增加值分配以及增加值出口,提高商品與服務的標準化與信息化水平。主要表現為在全球價值鏈的各個環節中,數字智能技術高度滲透于組織研發、設計、生產與銷售以及品牌運營等各個分工環節,能夠節省各個環節的交易成本以及實現諸如生產制造環節的智能化,降低勞動力成本以及增加服務端的增加值。具體而言,在數字智能技術影響下,在生產環節,生產設備與控制過程的全流程數字智能化實現標準化與個性化生產并存,范圍經濟效應與規模經濟效應得以放大,依托于信息智能技術能夠實現人力、物力與財力等各類資源的優化配置,最終帶來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各個環節的成本降低效應。同時,在全球價值鏈為基礎的國際貿易中,由于地理距離、語言文化以及制度距離等多種障礙因素的存在,傳統價值鏈傳遞過程中的交易與溝通成本較高,貿易規模受限。而數字經濟時代的數字信息技術尤其是互聯網平臺導致傳統貿易成本大幅降低,產業組織的多樣化包絡于數字貿易平臺之中,擴大了貿易的規模以及降低了國別之間的貿易成本。
第二,數字經濟對產業鏈的賦能與深度融合效應。數字經濟時代不僅僅在微觀企業層面體現為對企業生產與服務成本的降低以及貿易過程的成本降低,更體現為在中觀層面對產業鏈整體性的賦能與融合效應,通過重塑產業鏈內的分工邏輯以及運作模式實現產業間的功能互補與跨界協同,實現基于產業鏈的全球價值鏈的增值效應。具體來看,數字經濟時代最突出的數字智能技術便是高度的融合特征催生出制造業服務化,數字產業與制造業的融合發展激活了產業內的分工效率以及技術創新效率,產業鏈各節點之間的高度協同以及不同產業鏈的高度協同導致產業附加值不斷增加。尤其是制造業與服務業的邊界日益模糊,生產性服務業在數字經濟時代得以突飛猛進。且數字信息技術使得傳統產業鏈內的分工個性化與規模化并存,傳統高度模塊化與集成化的產業鏈能夠分解為多個產業鏈,且分解與擴張邊界主要是延伸出全新的創新生態,最終基于產業鏈的價值鏈得以增值。
第三,數字經濟時代對出口增加值的放大效應。數字技術通過數據傳輸以及信息系統的標準化運作,大大提高了商品與服務過程中的標準化程度,并提高了全球貿易與全球產業分工過程中價值鏈的靈活性。比如,傳統的基于國際貿易的過程需要經過海關各類程序的審查,國際貿易的通關時間限制了整個價值鏈活動的傳遞效率,甚至一定程度上存在較大的人為的交易成本。在數字互聯網技術下,貿易過程能夠實現線上與線下協同,各類審查能夠通過數字平臺納入統一的框架內容之下,實現審查的條塊分割轉向標準化與統一化。且在貿易的終端環節支付過程層面,數字技術能夠實現貿易時間縮短、貿易過程效率改善以及弱化地理空間距離帶來的不確定性,進而增強了增加值出口。總體來看,數字經濟時代下的全球價值鏈相較之于傳統價值鏈在各個環節以及衍生的附加值效應都呈現出全方位的變化。
二、數字經濟時代下全球價值鏈面臨的突出風險
(一)價值鏈空間布局:數字技術的深入賦能效應衍生全球價值鏈縮短與回流效應
盡管數字技術進一步為產業數字化與數字化產業化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數字技術將有助于企業的制造過程與研發設計以及售后服務實現深度融合,進而大大延擴了整個價值鏈與產品鏈的空間,為處于中低端制造企業攀登全球價值鏈中高端位置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但是,從全球價值鏈布局來看,數字信息技術的深入運用打通了整個產業內垂直分工與水平分工過程中的模塊化與標準化,且價值鏈的治理模式從傳統的消費者驅動、生產者驅動轉向了去中心化的平臺驅動模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低端分工環節在地理空間上的遷移成本,從這個意義上,這為處于全球價值鏈高端的主導國家以及主導產業環節實現其他中低端環節的空間布局收縮提供了廣泛的可能性。從全球生產網絡中的“美-德—中”制造中心來看,在近十年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下,根據ChristopheDegain等學者的測算,研究發現2005-2011年之間以美國、德國和中國的聯系緊密程度不斷攀升,但是這一趨勢在2015年后發生了逆轉,以美國為核心的北美生產網絡與中國為核心的“東亞+東盟”生產網絡日益分離,呈現出全球價值鏈的回流收縮以及孤島效應。
近年來,受到第三次工業革命下搶占信息網絡與智能技術的話語權的技術創新能力的競爭效應,以美國、德國為代表的處于全球價值鏈高端地位的發達國家紛紛布局新一代信息產業、數字產業(人工智能、區塊鏈以及工業機器人等)以及新一代生物技術作為搶占顛覆性技術創新話語權的重點領域,制定了“再工業化”等戰略強化鏈主國家在整個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鏈主”地位,比如美國近年來其整個產業政策的核心導向便是圍繞以“恢復基礎制造業,保護中端制造業和強化高端制造業”為目標強化其在整個全球價值鏈中的“鏈主地位”。
總體而言,數字經濟時代下的數字技術深入賦能全球價值鏈的各個環節,提高全球價值鏈分工效率與整體出口增加值的過程中,也為部分鏈主國家縮短全球價值鏈以及回流價值鏈中的部分環節提供了可能,進一步強化了技術策源國和“鏈主國家”的先發與先動優勢,導致部分發展中國家以及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的國家面臨“分工陷阱”以及回流帶來的“擠壓”風險。
(二)價值鏈治理:鏈主國家對“攀升國”的科技壓制與封鎖衍生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
隨著數字經濟時代下的數字智能技術成為驅動新一輪經濟社會變革的關鍵技術支撐,尤其是數字通信技術中的5G技術以及決定算力的芯片技術成為全球價值鏈中“鏈主”國家掌握數智經濟中價值鏈高端的關鍵核心技術,因此其排斥或者制裁鏈內其它國家的產業以及企業進入關鍵核心技術領域便成為近年來全球價值鏈治理中面臨的突出科技風險。
為穩固維持以美國為主的“鏈主”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高端位置,近年來美國以實現國家安全以及遏制中國全面轉型升級為目標,對中國數字通信領域的關鍵企業(軍工企業、大型民營企業以及領軍企業)、關鍵技術研究機構、關鍵高校實施系列制裁活動,全面遏制與封鎖中國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下搶占數字技術話語權崛起。比如,自2018年以來,美國商務部陸續對44家中國軍工類企業、華為、中興等數字技術領先型企業進行制裁與封鎖,出臺關鍵核心技術的實體管制清單以及限制重點高校的部分學科領域的國際學術交流合作,對新一輪工業革命的系列數字與智能技術列入出口管制清單,阻斷對中國的關鍵核心技術的供給,導致近年來我國在部分產業中的關鍵核心技術的“卡脖子”問題凸顯,其中“卡脖子”技術主要涉及5G、人工智能、軍工安防、芯片開發、超級計算機、網絡安全、工業機器人等新一輪工業革命下的顛覆性技術領域。
總體而言,全球價值鏈中的“鏈主”國家近年來對中國制造業的全方位的科技封鎖,加劇了制造業領域中的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且“鏈主”國家通過拉攏具備科技話語權的價值鏈高端的其他發達國家組建技術封鎖同盟,全面遏制中國制造企業攀登全球價值鏈中高端。
(三)價值鏈分配整體失衡:全球價值鏈分工環節的失衡與數字鴻溝加劇世界經濟不平等
在數字經濟時代,全球價值鏈最為突出的特征之一便是制造業的服務化,即從全球價值鏈的各個環節來看,由于數字信息技術的高度滲透以及對產業的深度賦能,傳統產業鏈中的生產環節高度自動化以及智能化,相應地處于生產環節的增加值便不斷收縮,而處于生產環節上游以及生產環節下游的研發設計以及產品銷售與品牌等價值鏈環節的附加值便不斷提升,制造業服務化程度也成為制造企業攀升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關鍵。在研發設計環節,數字化賦能研發設計能夠為企業的研發提供更多的知識服務,提升整個技術的復雜程度以及技術開發的效率;在銷售與品牌環節,數字化賦能能夠強化消費者以及用戶體驗,進而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因此,數字經濟時代下由于數字技術的深度運用以及對全球價值鏈的各個環節的深度賦能,最終導致價值鏈的“微笑曲線”中間收縮,兩端陡峭,加劇了全球價值鏈內企業的分工地位的不平等以及世界經濟貿易格局的不平等。
同時,由于數字經濟時代平臺企業成為價值創造過程中最為顯著的微觀組織支撐,平臺企業以其獨特的網絡效應、商業模式以及數字能力實現平臺壟斷,提高了具有數字平臺資本的數字強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價值分配地位,加劇了以跨境數字平臺主導的貿易不平等格局。比如,根據UNCTAD(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全球數字經濟報告2019》顯示,在2018年,全球市值超過10億美元的平臺企業總市值中,美國所占比重為72%;谷歌占有全球搜索引擎市場的份額超過90%;亞馬遜占有全球線上零售市場的份額約為37%。更為關鍵的是,在數字經濟時代,處于數字產業中的領軍企業具備了制定技術標準的技術話語權,能夠對整個價值鏈的其它企業實施相應的標準主導的技術干預或者技術標準控制,且領軍企業能夠利用其強大的數據、算法等技術實現對鏈內其它企業精準定價,最終通過算法技術實現跨行業的壟斷,進一步強化了“鏈主”國家中的領軍企業與鏈內其它企業在價值分配上的不平等。
三、數字經濟時代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應對思路
(一)生產要素驅動:強化數據要素的第四類生產要素在數字創新驅動發展要素中的核心地位
從生產要素的角度,數字經濟時代最突出的生產要素變化便是數據成為第四類生產要素。不管是數字產業還是產業數字化,其都離不開數據要素在整個產業價值鏈中各個環節的有效流動與充分配置,通過數據的收集、加工、處理以及轉化,能夠實現全新的數字資本以及數字賦能的智力資本。從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角度,價值鏈各個環節包括研發設計、生產制造以及產品銷售以及品牌服務等各個過程,數據流動是實現價值鏈賦能以及提升增加值的必要條件。數字經濟時代全球價值鏈的有效分工以及邁向中高端離不開數據要素在全球產業鏈中的有效配置。
但現實是,目前對于數據流動依然存在種種制度障礙以及標準壁壘,數據流動不充分以及缺乏數據共享機制成為制約傳統產業尤其是制造業深度數字化賦能的關鍵障礙,也成為我國在數字經濟時代制造業攀登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關鍵障礙。且從全球價值鏈中不同地位的產業分工體系中,不同國家的數據基礎設施以及對于數字技術運用的能力差異巨大,數字不平等以及數據鴻溝成為阻礙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國家邁向中高端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創新驅動以及創新引領的全新發展戰略下,我國政府以及企業需要高度充實數據要素在整個產業數字化以及數字化產業生產要素中的核心地位。具體而言,政府需要強化對數字技術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加強公共數據的共享平臺建設,尤其是在制度層面需要加快建設面向數據要素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體系,為數據要素在整個產業鏈與價值鏈中的充分流動提供制度基石,為構筑與強化數據要素的市場定價體系、流通體系、交易體系以及治理體系提供堅實的制度基礎。
更為關鍵的是,強化數據要素在數字全球價值鏈形成以及擴展升級中的核心地位,數據要素其價值的增值與放大依賴于數據要素與其它要素的深度融合,因此需要基于數據要素的供給規律,構筑堅實的數字人才基礎,激活數據要素的組合配置與生產的價值效應,這一過程最關鍵是加快實現數字人才供給體系建設,尤其是當前面前數字人才的公共創新體系尚處于起步狀態,政府需要加大對數字人才的公共基金扶持力度,推動創新型企業強化數字人才培訓體系建設,引導高校、企業共建數字人才培養基地與數字人才創新共同體。
(二)產業賦能:強化數字經濟對產業的賦能效應,打造面向國內大循環的產業鏈與創新鏈
在數字經濟時代,產業數字化是產業衍生附加值的重要實現方式,產業數字化的背后是傳統產業充分觸網,加速運用數字智能技術實現產業鏈。供應鏈以及創新鏈各個環節效率改善以及能力協同。當前面對中美關系的新形勢以及全球價值鏈雙端擠壓的新局面,在產業層面需要高度重視面向國內大循環主導下的產業數字化能力建設,將產業數字化作為產業基礎能力提升工程以及未來產業培育中的重中之重。在全球分工的碎片化價值鏈治理格局下,我國數智產業中的關鍵核心技術依然存在對外依存度高以及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等問題,因此面向內循環主導下的產業數字化前提依然是提升數智企業面向數字智能技術的創新能力建設,提升本土產業鏈中產業數字化的底層技術基礎。
目前,推動產業數字化轉型存在兩種主要路徑,第一種主要路徑是以傳統產業中的龍頭企業以及創新型領軍企業為牽引,通過打造工業互聯網平臺實現產業內各個分工環節的智能制造以及數字化轉型。通過設立“燈塔工廠”等方式對傳統制造企業予以數字化技術改造,提升傳統制造企業的機器設備、生產流程的數字智能化程度,并依托工業互聯網平臺有效實現各類資源的集聚與協同,實現供需對接,大大降低整個產業生態中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成本與運營壓力。
因此,圍繞第一種路徑需要大力提升領軍制造企業的數字技術創新能力,加大對工業軟件、工業數據共享平臺以及工業數據模型的開發力度,形成以工業智能平臺與智能軟件為核心的智能賦能生態系統。
第二條路徑主要是以數字平臺型企業為依托,利用數字平臺型企業的數據服務能力、云服務能力以及算法能力實現傳統制造企業的數字化改造,深入推動傳統企業的加工制造、工業模具、產品服務以及研發設計等各個環節的智能化,實現研發設計、生產制造以及物流倉儲的高校協同,并依托大數據分析能力實現供需匹配,提升大規模定制與個性化定制的柔性制造能力。
總之,數字經濟時代實現全球價值鏈攀升的產業基礎是產業數字化與數字化產業的雙輪驅動,構建面向內循環主導下的本土產業鏈與創新鏈的共促機制,以數字技術驅動的創新鏈與產業鏈的深度耦合與能力協同,全方面實現產業數字化轉型,最終攀登全球價值鏈中高端。
(三)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強化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建設驅動創新引領,破解關鍵核心技術的“卡脖子”問題
在全球價值鏈高度開放的分工體系下,在微觀企業層面面臨的嚴重問題便是開放式創新作為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企業的主導創新模式選擇。盡管開放式創新范式下企業能夠通過研發合作、知識吸收、成果租借、專利授權、許可證制度等多種形式規避技術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等問題,但是開放式創新的前提是整個創新環境處于高度開放的穩態之中,企業能夠通過在全球范圍內尋求創新資源實現創新能力的迅速提升,但是一旦全球價值鏈內的其他國家開放式創新環境惡化,處于技術領先地位的企業迅速從開放走向相對封閉,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企業難以在開放式創新環境中尋求技術替代方案以及技術合作的理想伙伴,最終整個企業的創新鏈面臨斷鏈風險,直接的體現是創新鏈的“鏈主”企業對全球價值鏈中的其他企業技術封鎖,直接導致了整個產業以及微觀企業的關鍵核心技術的“卡脖子”問題。
因此,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企業作為賦能全球價值鏈的微觀組織載體,也是整個產業鏈內實現產業數字化的產業組織,需要進一步提升數字企業的全面自主創新能力,將創新引領與創新驅動擺在整個創新戰略導向中的基礎性與關鍵核心地位,逐步擺脫舊有路徑中的開放式創新體系下的技術過度外嵌、過度依賴的技術引進、模仿與消化吸收模式。
具體而言,企業全面自主創新戰略不僅僅是企業家個體或者研發團隊的創新驅動導向,而是以綜合價值導向、人本意義與共益型創新的邏輯取代單一市場盈利邏輯重塑整個企業的創新底層邏輯,更是構筑整個企業的自主創新文化、自主創新管理制度體系、創新人才培養體系以及創新治理體系全方位支撐整個企業自主創新戰略的實現。
因此,全面自主創新戰略的落實不僅僅需要企業高度重視研發投入,設定研發投入在整個營業收入中的門檻值,更需要企業家以及整個企業戰略團隊超越企業競爭的單一市場視野,培育真正具有創新戰略眼光的戰略型企業家,將整個企業創新戰略體系放置于國家創新體系與產業創新體系之中,實現企業在自主創新過程中真正意義上契合國家戰略、引領市場需求以及創造可持續導向的綜合價值,實現企業向創新型企業以及世界一流企業轉型,最終以世界一流企業構筑全球價值鏈中的“鏈主式”競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