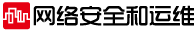“熊貓燒香”案一審以四名計算機病毒制造者、傳播者獲刑一至四年告一段落。由于此案備受關注,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出現該院有史以來刑事審判旁聽爆滿的情況。其中,有多家網絡公司人士申請旁聽,李俊等人到底該判什么罪,業內人士無疑最關心,而這種關注,注定事情還遠沒有畫上句號。記者今天就此采訪了一些法律專家和業內人士。
除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外,主犯是否還應被判盜竊罪
“熊貓燒香”案發生后,人們關于此案定性的討論就大量出現。一段時間以來,對于李俊是該重判還是輕罰一直存有爭論。
互聯網資深法律專家于國富早前分析認為,“熊貓燒香”作案者涉嫌幾重罪:李俊這種行為既竊取信息,又破壞計算機系統,有可能會定為“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和“非法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傳播病毒,并竊取財富,又涉嫌“盜竊罪”;“熊貓燒香”病毒在竊取用戶游戲賬號或者QQ號后導致原使用者無法使用,還可能會涉嫌“侵犯通訊自由罪”。
今天的庭審結束后,有專家表示,根據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利用計算機實施金融詐騙、盜竊、貪污、挪用公款、竊取國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關規定定罪處罰”,因此“熊貓燒香”案主角還應被判處盜竊罪。
之所以出現這樣那樣的議論,既是因為計算機網絡技術的復雜性,也是因為法律規定上的不完善。
行政法規及規章對病毒的定義能否適用于刑法
國務院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以及公安部出臺的《計算機病毒防治管理辦法》將計算機病毒均定義如下:計算機病毒,是指編制或者在計算機程序中插入的破壞計算機功能或者毀壞數據,影響計算機使用,并能自我復制的一組計算機指令或者程序代碼。這是目前官方最權威的關于計算機病毒的定義,此定義也被目前通行的《計算機病毒防治產品評級準則》的國家標準所采納。
但是,有關專家提出,刑法對計算機病毒等破壞性程序并沒有界定,行政法規和規章中的計算機病毒能否理解為刑法上的計算機病毒還存在疑問。
木馬是否屬于刑法規定中的病毒
我國刑法規定,故意制作、傳播計算機病毒等破壞程序,影響計算機系統正常運行,后果嚴重的,依照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定罪處罰。而網絡病毒中的蠕蟲、木馬是否都屬于刑法上的計算機病毒等破壞性程序,目前還沒有立法或者司法解釋。而根據上述計算機病毒的定義,網絡病毒中的病毒、蠕蟲屬于計算機病毒,但是木馬并不進行自我復制,因此不符合病毒的特征,不屬于計算機病毒,而它的危害性卻是巨大的,因為它包含能夠在觸發時導致數據丟失甚至被竊的惡意代碼。
有關專家認為,如果根據公安部的上述理解,將木馬解釋為計算機病毒是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的,而木馬是否屬于“計算機病毒等破壞性程序”,我國法律沒有對此作出解釋。而且木馬不單是破壞用戶的數據,還竊取用戶資料。此外,木馬還具有隱蔽性和非授權性,它能夠吸引用戶下載運行,一旦控制端與服務端連接,控制端將竊取到服務端的很多操作權限。如果將破壞性程序解釋為對系統的干擾程序,那么木馬屬于破壞性程序是沒有問題的。但如果將破壞性程序限定為對計算機功能和數據的毀壞,那么很多木馬病毒不能被認定為破壞性程序。這就使得絕大多數的木馬程序的制作和傳播在現行法律中都不能構成犯罪,而木馬就危害性來說絕對是不亞于一般計算機病毒的,這顯然是立法時所沒有預料到的。
木馬的大量出現對刑法的規定提出了挑戰,對刑法規定的破壞性程序必須作出明確的界定。
必須通過立法將木馬等納入破壞性程序范圍
網絡病毒的發展,使得刑法在這方面的規定出現了明顯的滯后性。因此,必須從刑法上明確網絡病毒的含義,通過立法或者司法解釋將木馬等形式納入破壞性程序的范圍。
前不久,在北京召開的“2007安全中國計算機惡意程序治理法律環境高層研討會”也認為:應進一步加強治理惡意軟件的普及宣傳工作、共同提高互聯網用戶的信息安全意識和防范手段;應進一步加強政府主管部門與互聯網企業、用戶之間在網絡安全立法、執法工作上的聯系和交流,共同推動國家在有關治理惡意軟件的立法、執法等方面的工作;網絡安全專業機構和各互聯網企業應加強研究與合作,積極為國家立法機構提供技術和信息上的支持,并配合司法機關加大對惡意互聯網程序的打擊力度。